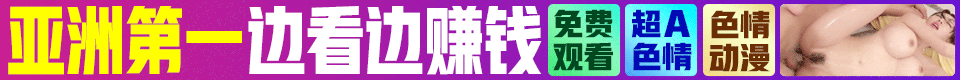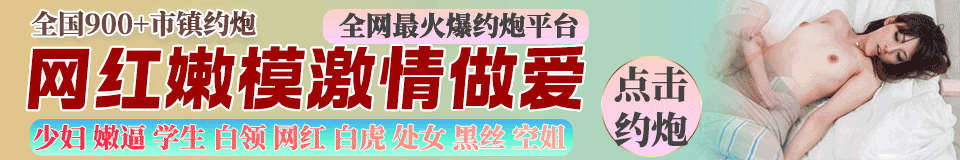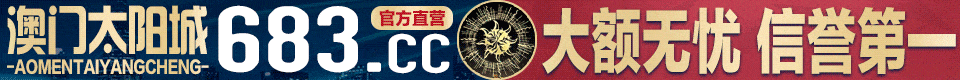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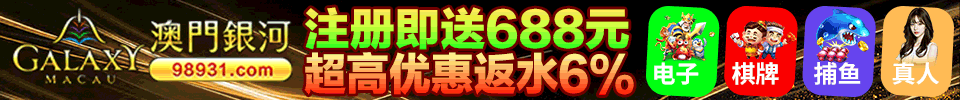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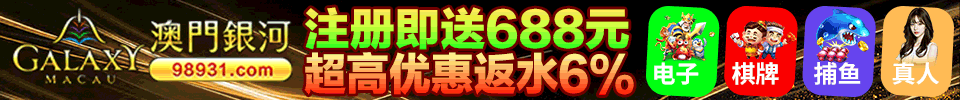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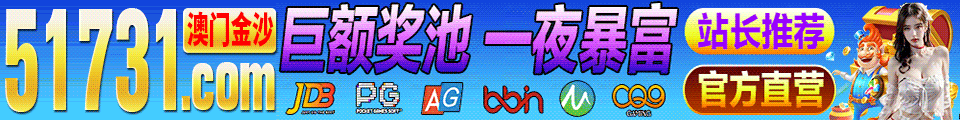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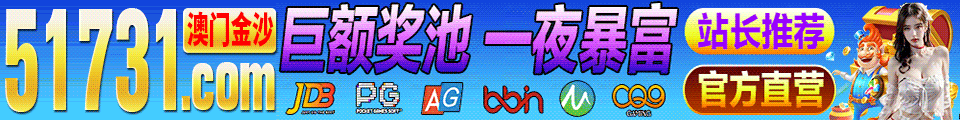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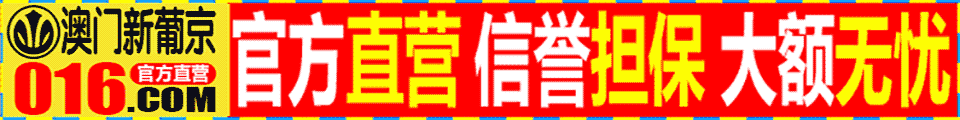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我和三姐的亲密关系】
(一)
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
这句话用在我对待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
我自己感觉着我还是个正常的人,四十多岁,事业有成,孝顺父母。虽然这
两年有了几个银子,但也没换老婆。除了办户口身份证从为进过派出所,甚至连
交通规则够不曾违反过。
但就有一样儿,见了小姑娘就心慌,我是说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在外面
单独遇到的时候,就会邪念顿生,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她,哪怕只
是简单地抚摸一下头,或者拉拉胳臂,熟悉的可能抱一抱,再熟悉的就逗她玩玩
儿,挠挠痒痒,捏捏屁股,但最期望的还是能看一眼她的小屄屄。
我对小屄屄有着至高无上的喜爱。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我童年时代,
孩子是八岁才上学,那时也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所以大街上的孩子很多,男孩儿
女孩儿一起玩耍,看屄屄的机会也很多。长大了以后,虽然也能遇到小女孩撒尿
的情况,但毕竟是大人了,不能驻足欣赏,稍微感到遗憾。若是自己的亲戚有个
女孩儿,那还能不好好看看,弥补一下我的心理缺陷?
就说我那年春节回家,初二去我三姐家,和三姐聊天,翻出了家庭相册看,
有我们姐弟几个的,有全家的,也有姐姐他们家的,翻出她女儿艳艳小时候的,
突然有一张令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一般都是男孩儿采取那样的姿势照,露出小鸡
鸡,很少见女孩也那样的,所以看到那小屄缝心里就痒痒半天,爱不释手。
男女的差别就在这里,小男孩十来岁光着屁股满街跑,没觉得怎么得;要是
小女孩儿也那样,我相信好多男人的目光会盯着那迷人的小缝。就像几年前看到
一篇文章说的,在奥地利首都普鲁塞尔中心广场不是有个着名的雕塑吗,一个小
男孩儿拿着鸡鸡撒尿,这背后的故事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
后来有些女权运动者呼吁男女平等,要求也应该造一个女孩儿撒尿的雕塑,
这个提案还真通过了,就在男孩旁边加了一个蹲着撒尿的女孩儿。可是观光者看
了总是觉得有说不出的滋味,看到小男孩儿撒尿,只会觉得天真可爱,可看到女
孩下面射出的那一道水流,往往容易产生不该有的想法。
艳艳五六岁之前三姐带她来过几会回。每次来了就会带给我不少欢乐,也带
给我不该有的心跳的感觉。
有一次我抱着她,突然撒尿了,小缝里射出一道水流,真想低下头去喝,就
是够不着。然后我说我给她擦,——这种事我是愿意效劳的。
擦的时候就扒着看,其实我也没怎么使劲儿扒,三姐姐知道我是故意想看,
心疼她闺女了,拍了我一下头:“这么大了你还改不了那毛病?!”
什么毛病?就是小时候喜欢抱着邻居的女孩儿看屄屄的毛病,好几回三姐看
见了。有一回可能是把小女孩儿弄疼了,哭着去找她妈,搞得我好没面子。后来
她妈来找我妈妈说这事儿。我在一边断断续续地听见几句,妈妈说:“小孩子懂
什么?!”
听三姐这样教训我,顿时脸上就火辣辣的。
“看看怕什么?”我哪能这样被教训啊,从小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受宠惯
了,姐姐们也不敢把我怎样。“那毛病还不都是叫你逗引的?!”
我这样说,三姐脸红了,朝向一边,不敢面对我。
三姐似乎在沉思。
我也被三姐的沉思带进往事的回忆中……
?
(二)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下应该有个哥,听妈妈讲生下来就夭折了,所以大姐比
二姐大四岁,后面都是二岁只差。
我不到十一岁时,我大姐就出嫁了,所以家里就只有两个姐姐,二姐勤劳吃
苦,三姐懒,调皮但和我关系最好,也因为年龄差距小。所以我和三姐玩耍的时
候多。
十来岁的男孩儿就对女孩撒尿感兴趣了,在街上经常遇到,瞅上两眼,还怕
被旁边的大人看见。但我没想到能看到三姐撒尿的景观是那么美!
一次我和三姐去挖兔菜,在一个壕沟的凹坡处,我猛然发现了三姐正蹲着撒
尿。
我的目光一下子就扫到了三姐那十分醒目的地方,它比我在街上看到过的任
何女孩的屄都美,怎么个美?当时形容不出来,反正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屄都更像
屄!就是说,它更符合我意念里的那个屄!
当时心就扑腾扑腾地跳,心里说看到屄了!因为很意外,所以很惊喜!
“看着人!”三姐这样说,分明没拿我当外人。
我警惕地想四周张望,没发现人,再回头看时,三姐已站起来,在她提起裤
子的瞬间,我看到了她光光的,迷人的三角区,那是我对女孩外生殖器的最初印
象,就是鼓鼓的三角下一道缝。
那是我多么幸福的日子啊!看邻居女孩儿的小屄被发觉几次以后,我就胆怯
了。幸好有姐姐,可是自己的姐姐总是不好意思。心里想看三姐两腿间的那个宝
贝儿,在姐姐面前又不好意思说出那个“屄”字来,就说“我想看……你的”,
或者“我看一眼”,三姐就明白了,十回有八回都成功。
三姐也不是立刻就脱下裤子让我看,磨蹭一会儿,羞羞答答地找个没人的地
方,蹲下装作撒尿,有时候真尿出来,有时候根本就没尿。那个年龄也知道姐姐
那儿不是供人观赏的,所以看的时候也不是趴在地上直直地盯着看。大约离开她
几步,只要能看到就一不也不多走。还要注意周围又没有人,我可不能让别人看
见三姐的宝贝儿。
从看见三姐解裤子的那一刻,心就突突地狂跳,每一次都在心里嘀咕:真的
吗?真能看到吗?
退下裤子的时刻往往是最羞人的时刻,我要是一直那样盯着她看,三姐很有
可能就不干了。
我就环顾一下四周,留给三姐一点时间,让三姐蹲下,也不敢太久,怕错过
了春光乍泄的大好时机,再转过脸来时,一幅‘春点杏桃红绽蕊’的美景就呈现
在我眼前了!那瞬间的视觉刺激是巨大的,浑身血液立刻就涌动起来,涌向特定
的部位,便产生了一触即发的冲动。
可那印象太深了,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三姐蹲着的时候,眼睛往往不是注意我,而是向四周观望。她膝盖往往比平
时撒尿时分开得略开一些,使得两腿间的光线不至于太暗,在两条白嫩的大腿的
牵扯下,那两片丰满的,最容易引起视觉刺激的肉唇恰如其分地开放着,间隙不
大不小,再大就显得太猥亵,再小了就觉得不解馋。
白嫩的唇泛起春色,粉红的蕊透着娇嫩,也勾引着我最原始的欲望。当薄薄
的尿流冲开那红红的小花瓣时,再也无法掩饰它的羞涩,发出“呲——呲——”
美妙的音乐……
那才叫闭月羞花呢!
当时就是不明白,三姐撒尿时,为什么流到屁股上,完了还得擦,真麻烦,
哪有我们男孩儿方便!
我就一报还一报,也叫三姐看我的,当着她的面翻起包皮,露出红红的头,
羞死你!!
可惜那样日子也就不到两年,后来三姐撒尿就开始躲我了,我估计当时她可
能长出屄毛了,所以才不好意思让我看了。
我手淫大约也是从那个年龄开始的,从此后我手淫时就有了想象的对象,至
于肏屄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有似乎无,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实践过,只是从骂人
的话里反映出一些意念的东西。
那时我狠人家骂我:“操你姐姐!”尤其那些没姐姐的这样骂,我就觉得吃
了大亏,就上去和他拼命!
奇怪我是在我的印象中没见过我二姐的屄。那以后我又看到过好几回三姐撒
尿,当时觉得有姐姐真好,可以看屄,就是骂人时吃亏了。
那个年龄在性意识这方面,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都是朦胧的,都好奇。但
我没有想到三姐有一天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突然提出肏屄玩儿。别说
是真做,单单听姐姐说出那两个字,就兴奋不已,因为姐姐们很少说脏话。
可是说归说,真行动起来难,我想三姐当时也是好奇,是想把肏屄这种模糊
的概念用现实证明一下。
三姐说提出那念头以后,靠着炕沿立着,并没有马上行动,气氛紧张着,我
总不能扒姐姐的裤子吧?
犹豫了一会儿,三姐说:“你别出去说,啊?”
我说好。我见三姐真的要来,我兴奋无比,然后三姐就还是那样靠着炕沿立
着,把裤子退到大腿上我看到三姐那诱人的缝。却害怕了,听三姐说:“来”,
我才凑过去,弯着身子触上去,好象触到了,只感觉到两股间嗖——的一阵儿快
意,我两腿发软,差点跪倒。
顿时,我们俩都很紧张。
过后我回忆起那一阵儿爽,觉得真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三姐再一次嘱咐我不要说出去。
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后三姐在也没要求和我肏屄,可我老想了。
不过我们经常相互看对方的生殖器,那时,我的包皮可以翻起来了。三姐第
一次看见我把包皮翻起来时很吃惊:“哎呀,怎么这样?疼不疼?”
三姐也让我看,但她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让我看,只有在撒尿时让我看,或者
当我要求看时,三姐就装做撒尿。好象在撒尿以外的场合让人看屄,或者暴露出
屄有一种犯罪感。
大约是那年麦收过后,二姐和三姐不知道因为什么打了一仗,还动手了,妈
妈很生气,骂三姐,当然不能先骂二姐,二姐大吗,三姐委屈地哭,争辩,妈妈
就打了她,三姐就气得跑了出去。然后我听见妈妈又埋怨二姐,二姐也哭。
直到晚饭三姐也没回来,我就害怕,以前就听说谁家闺女为了赌气跳井的,
上吊的,我怕三姐出事,吃了饭我就去找,终于在一个麦草垛边上找三姐,我叫
她回家,她不回,还在生气,我不敢离开,怕三姐想不开,陪了她一会,三姐叫
回家给她拿吃的,我高兴极了,就跑回家拿了快玉米饼子和葱,那时也没有好吃
的。
天已经黑下来,三姐就是不回家,我一直陪着,后来困难觉得太晚了,不回
不行了,我们就一起回家,把三姐领回家,我有一种成就感。
那年代我们一家人睡一个炕,就两幢被褥,爸爸做木匠,经常在外,我和妈
妈一个被窝,两个姐姐一个被窝。
那天因为两个姐姐打了仗,都赌气,谁也不和谁一个被窝,妈妈就叫我和三
姐一个被窝,二姐和妈妈睡。
那时姐姐们穿裤衩睡觉,男孩儿到十四五岁还光着屁股睡呢。
三姐还在生气,面朝墙躺着,我躺在一边,和妈妈睡好象应该的,和姐姐睡
觉得不自在,好象谁也不碰谁。
就在那天晚上,半夜里,我觉得三姐在玩弄我的鸡鸡,把我弄醒了,我感觉
到她的手还在那儿。鸡鸡正硬着。
三姐知道我醒了,手不动了,半天,我们谁也没有睡,我翻了个身,碰到三
姐,我感觉到她和我一样,光溜溜的,也没穿裤衩。
好象两个人心领神会似的,我三姐就面对面贴在一起,她也往身上贴,我也
往她身上贴。我就开始用鸡鸡顶她的屄,顶上去了,我们俩身子都绷紧着,就那
样好长时间坚持着,我和三姐都开始呼吸急促。第二天想起来还心跳。
到了晚上,我们还一个被窝,我们俩好象都不想睡,直到听见妈妈和二姐那
边打起酣,我们又开始行动,紧紧地帖在一起,那个年龄也不知道还能肏进去,
只知道那样就是肏屄。
第三天,两个姐姐就好了,我也就回到妈妈的被窝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三姐也开始疏远我了,不和我做那样的游戏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二姐也出嫁了。
三姐没赶上恢复高考就高中毕业了,我上高一时,三姐就有了婆家,是个当
兵的,也时回来探亲定的婚。随着长大,那些和三姐的性游戏的经历有时不敢回
忆,想起来怪难为情的。
如果仅仅是童年的游戏也就罢了。可怕的是我对三姐的依恋随着年龄增长已
经转化成对三姐的性倾向。
准姐夫回部队半年后就复员了,他来我家的机会就多了,那时我正准备高考
了。
一天我下晚自习回家,屋里漆黑漆黑的,刚进屋突然听见炕上有动静,有金
属的碰创声,我正害怕,看见准姐夫从里屋出来,问我放学了,我说学放了,然
后三姐也出来,他们就出去了。
我的心就开始剧烈地跳,我一进里屋就问到一股浓郁的性气息。
我的心开始慌乱,我意识到曾经发生了什么,我心生起一阵儿嫉妒,愤恨,
同时也兴奋着,我开了灯,似乎想找到一点证据。爬到炕上,四处端详,忽然看
见卷起的被子下露出一点布,我扯出来,见是三姐的裤衩,上面是湿的,那气味
我在无熟悉不过了。
那是男人精液的气味!
立刻,在我脑海里出现这样一个概念:“三姐被人肏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大姐二姐出嫁我没有感觉,也
许那时我还小。
我受不了别人骂:肏你姐姐。
可现在三姐真的被人肏了。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三姐会叫人肏的概念,怎么会
呢,三姐,是我的三姐啊!怎么会叫人肏了呢?
不一会儿,三姐回来,一进屋就径直上炕,我知道她是冲她裤衩来的。
她看到她的裤衩不在原来位置,从我背后一把抢过去,然后不轻不重地打了
我一捶,准备下炕。
这时,我突然就一下子搂住她,叫了一声:“三姐?”
我也说不清当时怎么了,心里觉得冤屈,我的声音带点哭腔。
我什么也没做,就那样抱着,三姐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住了一会儿,我放
开三姐,什么也没说。
那以后我沉默了,妈妈也看出来,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学习太累。
三姐也话少了,尤其在我面前,我们俩不敢朝面,都相互躲着。
从妈妈和三姐平日对话里我知道,三姐到秋天就要走,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幸好我考上了大学,那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气氛好多了,三姐也高
兴的整天笑,和我的话也多起来。
就在我要报道的前几天,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那天晚上,只有我们俩人在家,本来说话说得好好的,突然有一阵谁也不说
了,然后又奇奇怪怪两人的目光对到一起,那是姐弟间从来没有的对视。
接下来,气氛骤然紧张了!要是谁说一句话也好,要是谁没事找事走一个也
好。
可谁也没走。
我的心跳的好难受!
突然,三姐关了灯。
我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勇气,立刻扑到三姐身上……
一阵慌乱之后,我扒下了三姐的裤子,可当我也退下裤子时,我发觉我不行
了。
根本就没硬起来,过分的紧张导致的结果。
淡淡的光线下,我看到三姐那儿已经长出毛毛。
三姐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激动地压上去,用那软软的东西挤压着三姐屄上。
奇怪的是,虽然没勃起,竟然也射出来。
我顿时陷入了无比失落的境地。
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
第二天我惶惶不安,很后悔,很沮丧,我尽量出去,找同学玩儿。
直到我走,我们再没做过。
?
(三)
上大学后,尽管我后悔过,自责过。但每当看到书上乱伦的字眼,我都会兴
奋。
想起来那次为什么没肏进去,太伤自尊了!
虽然对三姐还有想法,但毕竟大了,觉得乱伦不时什么好事。所以我不敢面
对三姐,实在难为清,假期里回家也不到三姐家去。三姐回来我说完话就躲开。
我毕业分配到沿海城市,两年后我结了婚。当我第一次看到老婆那个时,我
怎么也看不出美来,怎么也不能和小时候三姐的屄联系在一起,简直不是一类东
西!这也叫屄?!毛太多,小阴唇颜色太深。
三姐在我结婚第二年,第一次来看我,那时,她又抱养了个女儿,因为头胎
是儿子,她一直想要二胎,但几次都被迫放弃。那年我儿子也刚出生。
尽管事情已过去多年,但我和三姐单独在一起时还是有点别扭,这是我依然
喜欢三姐。一般地讲姐弟间是看不出性感的,可我不是,我看三姐就很性感,三
姐长得也确实好看,三个姐姐她最高,一米七的个儿。
那天,我和三姐突然在茅房里相遇,她正蹲在便盆上。
见我进来,三姐微微一笑,我刚想退出,一想也没有什么必要。就在一边洗
手,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时刻。
从那天起,渐渐地,我和三姐之间又有了一种感觉,也许那感觉从来就没消
失过,两人在一起也不再尴尬。
我相信,在我对三姐有性倾向的同时,三姐对我也有,从那次她主动关灯就
能判断出来 .
现在,三姐好像也在等待打破僵局的机会。
我,好象不只一次地幻想肏姐姐:我的阴茎插到三姐姐的屄里……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老婆到附近县城办事去了,说晚上才回来。
老婆走了以后,我突然开始心慌,三姐的表现也反常起来,说话很温柔,不
像是姐姐对弟弟说话。
午饭后,三姐在床上哄孩子睡觉,我进去,凑过去看。
“睡了?”
“睡了。”三姐说。
我觉得心跳得好快!
三姐还趴在那儿没动,仿佛在等待什么。
我把手臂搭在三姐后背上,三姐也意识到了要发生事情,但什么也不说。
我猛地把她身子翻过来。
“干什么呀?”三姐呼吸急促地说,好象也不觉得太意外,接下来的三姐的
表现更象是早有期待。
急不可待地扒下她的裤子,分开她的腿。
长这么大,头一次以主动的角色看三姐的屄,尤其兴奋!
不是我吹,三姐的屄真的很好看,三角区域很凸,毛毛只长在阴甫上,大阴
唇上很少,白白的很丰满,当然小阴瓣已不再是粉红的,但我还是喜欢。
我近似下流地扒开三姐的屄看着,好像要找回童年的感觉。
“有什么好看的?”三姐难为情地说。是啊!哪有弟弟这样扒着姐姐的屄欣
赏的!
我俯下头亲了一口,调过身子。
三姐好象没敢想弟弟会真的肏她,我相信她想过,但没想到会真的,尤其是
过去多少年了.所以当我压上去时,三姐显得好慌!
还没肏进去就气喘吁吁……
说实话我也很慌,喘不上气来,自己都不敢相信真的要肏姐姐了……
我找准了位置,好象对那次失败的报复似的,狠狠的刺进去……
三姐微微闭着眼睛,张着嘴轻轻的感叹一声。
我发觉三姐的阴道里早已准备不少淫水。
乱伦的刺激令我们格外兴奋,我猛里地抽动,从进入的那刻起,三姐表现出
了姐姐不该有的兴奋,甚至说放荡。
她不住地感叹!不时地呻吟出声,那感叹是对我性器官的赞美!
我们被彼此的兴奋相互感染着,那天我的阴茎也格外争气,奋力穿刺了那么
久,依然感到底气充足。
三姐压抑着呻吟,显然在弟弟身下发出那种呻吟是很难为情的,但是却不得
不发出来。
在我痛快地把精液射到三姐阴道里的那一刻,三姐几乎要喊出来。
我非常痛快,和老婆都没这样痛快过,我支撑着身子,看着三姐,我相信她
也达到了高潮,她依然在气喘.我觉得我当时脸上一定是一幅很得意的面容!
隔了十几年,三姐终于真的让我肏了一会!
真他妈的刺激!真他妈的过瘾!!
…………
?
(四)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以后,我和三姐又做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那么刺激,那么兴奋。
…………
眼下,我见三姐红着脸沉思着,心里有种说不的得意,真想把三姐压在沙发
上。不过,我的心思更在艳艳身上。
我两手抱着艳艳,举过头顶,在她小屄屄上亲了两口:“就是喜欢吗!管得
着?对不对,艳艳?”艳艳咯咯地笑,那时她才不满两周岁。
放下艳艳,让她自己玩儿去,我凑到三姐眼前,和她面对面:“是不是叫你
逗引的?”
“坏东西!”三姐笑着一把推开我,“从小你就坏!”
哈哈!三姐又一次被我打败了!
从那以后三姐就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知道我也不可能对艳艳作出过份的事
情。
我只要一有机会就欣赏艳艳的小屄,总想伸出舌尖舔舔那粉红的肉肉。其实
小女孩没有性意识,也就没有防范的概念,并不会意识到你再对她做什么。当然
我也不会对她做过分的事,望着她那稚嫩的身体,就像刚刚生出的豆芽,知道嫩
却不忍心吃,总是盼着它再长长,再长长……
五六岁的艳艳最可爱,嘴巴也甜,不时地叫着“舅舅,舅舅”,只要你给她
个笑脸儿,她就没大没小,老缠着你,在你身上一刻也不停地闹,经常把我的裤
裆捣鼓得盛起来。有时拿着东西往我嘴里送,我就连她的小手指一起咬住,稍微
疼点她就叫起来。为了哄她高兴起来,我就让她咬我的手指,将食指伸进她小嘴
里,心里的感觉又好像不是指头……
当需要某种刺激的时候,我就让她坐在我腿腰的弯曲部,硬起的鸡巴隔着裤
子顶在她小屁屁上,故意逗她高兴,那样她就来回晃动的身子,好像给我鸡巴做
按摩,好舒服!幸亏我岁数大了,要是十几岁那阵子,非被她‘按摩’出精来不
可。
老婆那时已经到外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三姐来是受妈妈的嘱托,来特地照
顾我几天,从小在家被疼爱惯了,妈妈不忍心让我自己做饭,所以三姐来了,我
就享福了,比老婆还好,在老婆面前得装大男人,在姐姐面前可以当小弟弟。孩
子们不在跟前,我就像小时候那样,趴到三姐背上:
“姐姐,好姐姐,给我做好吃的吧。”
“哎呀——你几岁了?”三姐依然像哄小弟弟,把握得手从她脖子上拿开,
我就转过脸去,在三姐脸上亲一下,三姐就赶紧从我的怀里解放出来,不然我就
会有更多的要求。
当有欲望的时候,我还是那样趴到她背上:
“姐姐,好姐姐,我想肏你了。”
“哎呀——你这不要脸弟弟!”
“我要姐姐就行了,要脸干什么?”
通常这种关系不被人理解,姐弟间怎么可以这样呢?可是发生了以后也没觉
得怎么内疚啊,不洁啊什么的。就像我小时候那年代,没有现在这样开放,什么
也不懂,听说谁谁两口子曾经是同学,也是不理解,同学怎么成夫妻呢?怎么好
意思啊?!
无论和谁,初交以后的第一次面对面总是难为情的。想想怎么真做了呢?真
的做过了吗?有时想起来也不大敢相信我真的肏了姐姐。常了以后也不觉得难为
情了,姐姐还是姐姐,弟弟还是弟弟,只不过增加内容而已,而且这内容还很刺
激!
“姐姐,晚上我搂艳艳睡吧?”
三姐说好啊,可真到了睡觉的时候,三姐又显得不太乐意。
“放心吧!”我说,“我还能怎么样她吗?”说完,又觉得自己心里那点儿
肮脏想法还得表达出来。于是又试探着说。
“反正又不是你亲生的。”
“不是亲生的也亲啊,小狗小猫从小养大还亲得不得了呢。”
“知道她父母是谁吗?”
“知道。就是后街上那个刘……你出来这么多年了,说你也不知道。”
“那……养大了人家再要回去怎么办?”我真想说还不如给我呢,多少年就
有抱养一个女孩儿的的想法,只是政策不允许。
“那就看孩子自己了,大了她愿意跟谁就跟谁吧。”这话一出口,三姐脸上
略过一片伤感。
晚上三姐给她洗了澡,她兴奋在澡盆里不出来,一个劲儿地扑腾水,等她闹
够了,我把她抱出来,给她擦干身子。
“艳艳,今晚在大床上睡吧?”我盯着她那小缝,看上去更像个屄了。
“好!”她高兴地在床上跳几下。我心里就更美了,恨不能也上去蹦几下!
三姐给她喝完奶,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和三姐看了一会儿电视,心早已按捺不住了,我说睡吧,三姐说:“我怕她
半夜醒了哭。”
“不要紧,哭就送过去。”见三姐还有顾虑,我就安慰她:“放心吧,我就
是喜欢喜欢她呗,从小都是大人搂我睡,从来没搂着小孩睡过,儿子从小就不让
搂。”
提到小时候,便想起了那次……
“还记得小时候咱俩一个被窝儿……”我凑到三姐耳边挑逗着。
三姐神秘地笑着。从小就喜欢三姐这样神秘的微笑,因为它总是让我得寸进
尺:“说实话,你当时想不想我肏进去?”
三姐羞得不知所措,在我大腿上掐一下:“快去睡吧,讨厌!”
我洗漱完毕,往卧室里走的时候,心就开始剧烈地跳,其实我并没打算做什
么坏事,那么小,还是自己的外甥女,我能做什么呢?所以各位看官,如果你期
望我奸淫我的外甥女,那是不可能的,你就到此为止吧,别往下看了。
从来还没有搂着这么小的女孩儿睡过,脱衣服时兴奋得不得了。只剩下裤衩
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不脱吧。
替她正了正枕头,望着她熟睡样子,俯下头亲了亲,躺下,把这个小肉蛋蛋
搂在怀里,和这么小的女孩儿肌肤相亲,还是头一回,不好说是性感,只是觉得
特别舒服。怪不得小时候妈妈就愿意搂我睡呢!
既然已经搂在怀里了,就体会体会她的肌肤吧,这样也不算过分吧。我记得
小时候妈妈搂着我,临睡前总是习惯性地摸摸我的蛋蛋,在我们那一带农村里,
大人喜欢小孩儿也都是这样,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哪里,看见邻居抱着个小男孩
儿,就凑过去逗逗他,伸手摸摸蛋蛋,那表示喜欢,也让小男孩儿的主人感到有
儿子的自豪。
也有发生误会的时候,一般是外村的,见了又认识,不问人家抱着的是个男
孩儿还是女孩儿,伸手一摸,感觉异样,自己很尴尬,主人也不好说,赶紧夸奖
几句,离开后暗暗地庆幸,无意中摸了个小屄儿……
这样想着,手慢慢地从她后背上滑下去,小孩的肌肤真可以用如脂如膏来形
容,尤其那小屁股,肉感很好,软软的,抓在手里像抓着一个成熟女人的乳房。
从她大腿外侧转移到内侧,心跳就开始加速了,再移几寸就是小屄屄了。
停顿了一会儿,并不是不敢摸,也不是不想去摸。当你面对一种美,一种你
向往已久的美的时候,你会因崇拜而产生对它的敬畏。
多少次想做贼一样窥视,多少次像色鬼一样把手伸进的私处,每每这个
时候,就有一种东西在击打着我心灵深处。
从十来岁开始产生性意识,到对姐姐产生性倾向,在我童年的蒙昧时期,像
俄狄浦斯一样,我对大自然所强加的这些违背道德的欲望毫无所知,待我长大以
后,我发现我的这些欲望已无法克制了。
艳艳那均匀的呼吸所产生的气流,温馨地撒在我胸脯上,带给我的却不是我
对她的父爱的体贴,而是一种欲望的上升,我几次都想把那不该有的欲望压抑下
去,但几次它又生起来,在这种欲望的暗示下,我的小指慢慢地脱离了群体,趋
向那感觉异样的肉唇,在它的带动下,另外四个指头也开始向那里移动,像是一
群狼在包围一个猎物。
当小指感觉到起伏凹凸的时候,我身体另一个部位也被充分地激发了……
中指陷落在小沟里的时候,就再也不想移开了,渐渐地埋进去,轻轻地划动
起来,涩涩的,没有成熟女人的那种润滑感,更想是在探索它的成长过程……
我越来越感到有退去裤衩的必要。
抬起头,端详了她一会儿,睡得好香。
好想去亲亲它,也许略微过分了一点儿,但也能说的过去,不就是喜欢喜欢
吗?
于是,我缓缓地向下移动身体,拱进被窝里,轻轻地分开艳艳的腿。
我虔诚地俯首下去,如同教父亲吻他的信徒般地凑到她小屄上,亲了一下,
嗅到那里散发出的幼香,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再一次凑了上去,黑暗中,伸出舌
头,用舌尖试探着那缝里的内容……
要是艳艳会做性梦,那今晚一定是一个美好梦境了。
裤衩被充涨得很大,自小腹以下,感觉到体内热乎乎的发胀。
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再搂过她来,把那热乎乎的发胀的部位贴到她身上,
心想就这样搂住她睡一晚上,也是难得的美事。
可是搂了一阵感到不行了,必须超越某种境界才能睡着。从九岁学会手淫之
后,好像不玩儿鸡鸡就不想睡,而一旦玩起来不超越那种境界还睡不着。
寂静的深夜里,好象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要是艳艳是我的女儿,我会怎
么做?我会进一步对她猥亵吗?我会搂着她想入非非吗?
可惜我没有女儿,我不知道那样的感觉,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遗憾。
接触一下也过分吗?即使有点过分,只要不进去,就不会伤害到她,何况她
在无意识中,也不会对她造成心理的伤害。而且身体的某个器官发出的信号,让
我觉得接触一下的迫切感。
松开怀里的艳艳,将她放平的时候动作故意加大,见她毫无醒来的意思。在
这个时候,对好人来说,怕要用相当的勇气来支持下面的行动,但对我这个畜牲
来说,只需要将裤衩脱去就可以了。
扯过我的枕巾,轻轻地铺在她屁股下面,然后翻身上去,拱着被子,身子下
形成一个大的空间,依稀能看见被我分开的两腿和那隆起的阴阜……
腰臀向下弯折……
在这种姿势的支配,不再需要用手拿着器官,而且在正常性交的时候我也一
向不喜欢用手拿着往里送,除非不得不那样。我喜欢最本来的,像自然界的动物
交配那样,经过一番探索顺其自然的进入……
接触到了,蜻蜓点水般地爱抚着她的小屄屄,像小时候雨后赤脚趟过泥水般
地惬意。记得我第一次在意识清醒下的,没有通过手淫的射精就是在这样接触时
发生的。可现在没有那时那么敏感了,只有插入和抽动才会到达那样的境界。
我注意着艳艳的反应,就算她醒来,朦胧之中她也不会意识到我在做什么,
不过即使真的想插入也不大可能。在这样的判断支持下,我将那轻微的爱抚变成
实实在在的亲密触动,试探着将龟头埋进那向往的缝里,好像感觉来到她那不太
明显的入口处的凹陷……
心越来越激动,阴茎的悸动越来越频繁。
稍微增加的力量不至于进去吧?
试着顶了顶,果然,感到龟头被前面的障碍挤扁了,不能再用力了,不然肯
定会撕裂她那稚嫩的阴门儿。
我也不敢那样坚持,怕控制不住真的抱着豁出去的想法冲进去……
稍微抬抬身,让龟头自下而上划上来……
开始的那美好的心情变成了一种折磨!
想进又不敢,不进又满足不了龟头对小屄的渴望!
艳艳啊!你要是现在十一了该多好啊!——不!哪怕你九岁,舅舅今晚也豁
出去了!大不了让三姐把我当作畜牲骂一顿。可那年当我把鸡巴插进三姐的屄里
时,在别人看来我已经是畜牲了,但我不后悔!
因为那种强大的心理刺激不允许我后悔!而让我后悔的是小时候三姐在被窝
里和我做操屄游戏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插入,真他妈的苯!其实也模模糊糊地意
识到应该能肏进去的,不然都长鸡鸡算了,干吗女孩儿还要长个屄!
射了吧,射到她的小屄缝里,贴得紧一点射,即使屄眼儿再小精液也不可能
一点都进不去……
这样想着,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另一只手开始手淫,竟然没费多大功夫,
那快要冲出的紧迫感就产生了,我再一次弯下腰臀,龟头实实在在的顶在小屄沟
里,瞬时,一阵阵剧烈的冲动蓬勃而出,身体几乎失去支撑……
太危险了!差点就捅进去了!
艳艳出声了。我赶紧下来,叫了她一声:“想尿尿吗?艳艳?”
“嗯”她朦朦胧胧地呢喃着。
“舅舅抱你去尿?”
“嗯。”
我披上睡衣,抱起她,顺便给她擦了一下,朦胧中的她也没有发觉,去了卫
生间,开了小灯,不止于刺着她的眼睛。
我勾着头去观察,没有发现血迹,也就放心了。
把她重新放回到床上,她很快就回到梦乡。我摸摸她原先躺着的地方,虽然
铺了枕巾,依然湿透了,床单上有一块湿润。忍不住再起身,凑到她小屄上,闻
到一股浓郁的精液的气味,才心满意足的躺下。
穿好裤衩,将身子躺实落了,体内的紧张已经消除,暂时不想理身边的小肉
蛋,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以后艳艳两年没有来,原因是她上学了。
我回老家见到过她,都是过年见的时候。孩子变化很大,对我来说,最大的
变化就是疏远我了,好歹用东西哄着叫了几句“舅舅”,摸了她一下头,心想往
后就更懂事了,那样的机会不会在有了。
九岁那年,三姐一家就搬到县城住了,三姐夫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别看人长
得不好,当初我妈妈不同意三姐这门亲事。可三姐有福啊,从小在家里就懒,找
了个婆家兄弟们多,也和气,基本不用她下地干重活。
三姐夫开始修车,赚了一笔,后来又在县城开了家饭店,生意逐渐壮大,日
子更好过了。
【完】